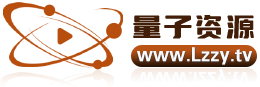《酱园弄》砸掉了《好东西》们的市场 -
近来热映的电影《酱园弄》引发了诸多争议。这部从诞生起就因全明星阵容、民国奇案题材而备受期待的大片,上映后却并未收获应有的票房与口碑。恰恰相反,全明星阵容不仅没有如预期般带来票房号召力,反倒因为片子在叙事逻辑、价值表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,既拉低了主角本就不多的路人缘,也让本片从一开始精心宣传的“女性觉醒”陷入到“虐女”的舆论漩涡中,不少观众认为影片过度渲染女性遭受的暴力与苦难,却缺乏对苦难背后社会根源的深入探讨。

不仅如此,有评论者也从主角詹周氏的真实人生经历出发,细致对比了影片对其经历的片面截取与故意删改之处。客观而言,杀人故事本身并不离奇,离奇的是詹周氏杀夫一案先后经历了汪伪政权、蒋介石政府、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,最终在人民政权的庇护下,她得以安然活到90岁。但影片却将重心放在展现本不复杂的案件及破案过程上,这种叙事选择背后,暗藏着主创们难以言说的“用心良苦”。
当然,这些角度都可以成为分析电影的切入点。不过,笔者认为,以上批评还远远不够到位。本片在创作中刻意篡改历史细节、画面充斥猎奇元素,上映之后又引发粉圈内斗、恶俗营销等争议。种种乱象的背后,固然有主创团队及资方的私心算计,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极少被舆论提及的核心问题,女性故事正在成为一门生意,一门服务于城市宣传、资本牟利的生意,而与任何真正的社会进步、价值正确与公平正义毫无关联。

那么,这门生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?笔者认为,其核心逻辑之一,便是以女性主义为光鲜幌子,行城市宣传之实。这可以被称为中国特有的“城市女性主义”:特定城市的文化资本娴熟地移植那些或凄惨或欢乐的女性故事,将其包装成具有普遍性和“正确性”的历史叙事。(免喷声明,本文的讨论只针对“城市女性主义”电影,不讨论“女性主义”本身)
这种叙事不仅垄断了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解释权,更试图推销一种“现代生活能解决所有问题”的万能方案。从之前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《爱情神话》《好东西》,到如今的《酱园弄》,我们能清晰看到这种运作模式的延续性,主导资方的地域构成大同小异,对历史书写的雄心也如出一辙。哪怕片方总能以“虚构故事”为借口搪塞质疑,可宣发阶段反复强调的“民国四大奇案之一”的标签,以及片尾“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”的免责声明,反倒像不打自招,暴露了其借“真实”之名行城市宣传之实的深层意图。


为了让这一“城市宣传”的叙事成立,影片在历史情境与阶层刻画上进行了刻意的篡改与扭曲。从历史情境来看,日伪统治末期,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在历史地平线缓缓浮现,那个行将朽木的日伪国家机器正处于摇摇欲坠的崩溃边缘。
詹周氏恰恰在这个时间点选择杀夫,这一情节设置暗合了革命/历史叙事的常见终点——旧秩序崩塌前夕的反抗。影片中,律师、记者等代表“公正”的势力纷纷粉墨登场,其行动确实能带来一时的大快人心,也让观众不难预见到最终结局:一桩本不复杂的案件,最终得到清算与审判,恶势力黯然退场,小人物虽有错却得以昭雪。
这种叙事模式与张艺谋有多大相似之处暂且不论,但熟悉历史的人会敏锐地发现,这种“三不管”的权力真空格局,根本不符合当时上海的真实境况,反倒更接近香港的社会生态。退一步讲,哪怕抛开对发生城市的错认,只要故事的时间点稍有延迟或提前,这个精心构建的叙事根基便会彻底崩塌。

而在阶层叙事上,影片的刻画则更为刻板与僵死。我们在片中看不到阶层应有的立体呈现与多元剖面,相反,底层群体永远陷入无意义的内耗,善良的女性平民总是被邪恶的男性欺骗与压迫。光线昏暗的阁楼亭子间里,邪恶欲望在阴影中蠢蠢欲动,处处暗含着罪恶与丑陋。暗合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及“底层蝼蚁”的文学形象。
而法庭、记者工作间却被塑造得金碧辉煌、光芒万丈,程序正义、言论自由一应俱全,仿佛那个时代才是正义与文明的化身,搞得今天的中国反而像是开历史倒车。女主角詹周氏挣脱牢笼的希望寄托之地——纱厂,更是被铺满柔光,营造出一种虚幻的美好,颇似古典好莱坞电影中的梦幻王国,完全抹去了历史上包身工们在其中遭受的非人剥削,不见半点血汗工厂的真实痕迹。
这么一套文过饰非下来,观看本片的观众不难留下这样的印象:所谓有识阶层所到之处,无不体现体面与文雅;而工农阶级的寄托之所,若非粗鄙不堪,便带有野蛮、凶狠的穷凶极恶之相。

这种对历史与阶层的刻意扭曲,本质上极为陈旧与俗套。电影这么做,是为了塑造一种“精英拯救底层”的虚假叙事,而这与真实的历史图景相去甚远。
在民国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、绝大部分情况里,法官、记者等精英阶层并不如本片所描绘的那般完美无瑕,他们始终无法脱离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束缚。倒是被新闻系认祖师爷时,才会显得“铁肩担道义”。
当时的社会现实是,黄色小报凭借猎奇八卦漫天飞舞,诉棍讼师为牟利而遍地开花,这才是常态(可以参考港台媒体圈娱乐圈)。一旦涉及女性议题,这些精英更会极尽专业之能事,造谣诋毁、搬弄是非。不仅是名人常受其害,就连普通女性也难以逃脱这种舆论暴力的魔爪。即便是詹周氏杀夫这一具体案件,《申报》等当时的舆论主流媒体给出的评价仍是“惊世骇俗”“世风日下”,而非影片中精心塑造的“公正发声”形象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对历史的曲解并非偶然。考虑到编剧是某系媒体出身,我们或许能从其成长背景与认知体系中,理解这种故意扭曲历史的深层动因。这更多的是主创团队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投射,而非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呈现。

正因如此,剧情硬往与“GHG”相关的进步叙事上靠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哪怕在剧中被捧上天的作家苏青,与汉奸陈公博有着难以撇清的干系,哪怕上海文化精英在历史洪流中早已四处流散,拯救主角的有关人士可能并不是“进步”势力。主创们依然能巧妙地,将一个本无太多深刻思想,把五四主旨当经念的女记者/作家,塑造成进步与文明的典范。正是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刻意改写,一个原本非常简单、远称不上悬案的杀夫事件,才被成功包装成一部商业大作,从而为“城市宣传”与资本牟利服务。
进一步看,影片的画面审美、故事走向乃至人物形象的胡编乱造,都在不断强化这种“虚假解决方案”。从内容内核来看,影片兜售的是一种精英主义价值观。当平民落难、孤立无援时,是当时可归入有产阶级的姐妹伸出援手,为其拖延时间,最终等到了解放的曙光。而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女主角,除了卖惨、被动等待他人拯救,几乎没有太多主动抗争的行动与办法。
那些毫无意义的暴力情节,不明所以的黑猪拱人画面,完全没有服务于故事主线或主题表达,更像是参演的大花小花们,为迎合所谓“主流”审美,向进步主义递交的投名状。演员们的表演,看似政治正确且演技在线,实则像极了那些年苦于拿不到奥斯卡奖项的小李子,乐于通过搔首弄姿、挤眉弄眼的夸张表现,恨不得将眼珠子都“蹦”出来,以证明自己会演戏。这种表演与其说是在塑造角色,不如说是为了瞄准时势及个人职业发展的潜在需求。

这种被情绪与奇观堆满的叙事,最终彻底导向了宣传与宣泄,而非对社会问题的真正探讨。导演似乎从未深入思考过:被剥削阶级,一定要通过被剥削的场景来展现吗?暴力,只有暴力的形式才能表达么?进步主义,是否只有通过苦难来表现其正确性?这也暴露了主创的短板,擅长拍摄商业片、江湖片的导演,其实无力真正体察性别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。

对无产阶级悲情的凭空捏造,对精英阶层、职业的“施舍”的渲染,必然会引导受众得出“只有阔太太才能拯救女性”的荒谬结论。而对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、历史革命等主题,导演既缺乏呈现的能力,也没有深入挖掘的意愿,甚至对当时黄土高原上真正开展的阶级、性别革命实践,想必也缺乏足够的认知与共情。
当影片的核心目标锁定为城市宣传时,其最终沦为一部城市宣传片也不足为奇。于是,一场在全世界都堪称罕见的滑稽场面出现了,一部本应反映女性悲惨境地的电影,其取景地居然成了网红打卡景点。铺天盖地的文旅广告、详细的打卡指南,清晰地告诉我们,这绝非女性电影的胜利,更不可能是女性群体的胜利,而是精英主义的胜利,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宣传胜利。
它与社会进步无关,也与城市的真实历史无关。将城市形象与进步主义强行捆绑,最终只能倒向一种城市主义的狭隘叙事:仿佛是城市本身给予了性别平等、群体解放的机会,而非群体自身的抗争与历史进程的推动。


这种创作及宣传模式,可以称之为“小红书电影”。果不其然,除了“城市宣传”,小红书等平台还在强调其与“五四女权”的关联,这也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存在明显偏差。五四时期的先哲们,并不提倡通过暴力杀夫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来换取独立。陷入宿命循环自不用说,自毁的方式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。
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选择自戕,其行为的核心是表达个人人格独立的愿景。女权先驱秋瑾,与丈夫因价值观分歧多有抵牾,面对丈夫吃喝嫖赌的恶习,她选择的反抗方式是投身革命事业,而非手刃仇人。
即便是在影视作品中,经典也并非如此呈现:吴永刚拍摄的中国影史杰作《神女》中,阮玲玉饰演的经典民国女性角色,并未遇到“GHG”式的神仙姐妹,真正能抚慰她心灵的,是基于阶级共情的关怀与超越时代的优秀教育家的引导。历史事实不会允许相关人士,凭空捏造出脱离阶级背景的“集美”群体,更不会承认“中产拯救无产阶级,社会精英维持社会安定,而无产阶级只能卖惨谋生、等待别人大发慈悲”这种荒谬图景。

《神女》
这就是上海城市的“女性主义”做题公式。要么在同一阶层内强调“we are family”的虚假团结,要么以高阶层视角俯视众生、展现悲天悯人的姿态。一到了胜者结算的页面,最终如同好莱坞明星那般洋相百出。个别人出演人民教育家张桂梅的故事后,马上将其拉入自身的共情范畴,到了颁奖典礼上还不忘边致谢边热泪盈眶,得奖之后欢天喜地,豪饮狂欢。
可一旦将目光投向消费主义与阶层分化的现实,这种为人所歌颂的上海式女性解放叙事便不攻自破了,它实则产生了对更多劳动者的隐形歧视,遮蔽了更多普通“她们”的真实声音与生存状态。
这种套公式做题的叙事模式,无论女性处于什么年纪都安排“娜拉出走”的情节,动辄以杀夫、旅游、谈恋爱来定义女性解放,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,并不会得到太多的认可与承认,只会成为被一个阶层、一个群体用来装扮自身的洋娃娃。
说到底,《酱园弄》的争议从来就不只是一部电影的好与坏这么简单,它更暴露了资本与城市宣传如何消费女性故事:它们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,扭曲真实的阶层关系,制造虚无的虚假希望,最终让女性故事沦为牟利与宣传的工具。

又是欢喜传媒,从《爱情神话》到《好东西》到《酱园弄》,徐铮实际上是这几年多数人没注意到的,”城市女性主义“电影潮背后的隐藏赢家
而这种工具化的叙事,恰恰与真正的社会进步、价值正确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。这恐怕不是所谓的“GHG”进步叙事,而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,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,成为被消费的对象,甚至被人卖了,还在替别人数钱。
不过,这两年电影行业动辄出现要完声音也证明了,这种致力于把更多普通人赶出电影院的“进步主义电影”就是在吃饭砸锅,前面的人能吃到收割红利,后面的人多数就要丢人又现眼,输人又输钱。进步主义神教再这么搞,最终大概就是成全别人的进步罢了,甚至电影连同“城市女性主义”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结局,都是可以料想到的事情了。